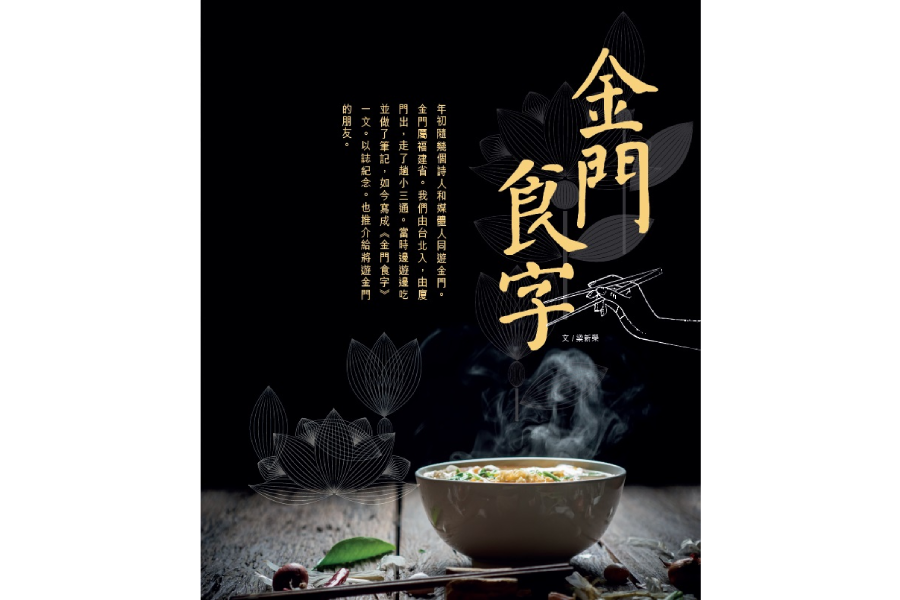萊比錫 —— 古典音樂的殿堂
德國萊比錫(Leipzig)原是一座供奉古典音樂的殿堂,五百年來香火不絕。六月過了一半,巴赫音樂節進行得密鑼緊鼓,不止把他老人家的圓臉印製成海報,張貼得滿街滿巷,火車站裡,一個白身藍底的巴赫像橫攔在出口,孜孜提醒來客別忘記到票房輪購,自動電梯上面,另外兩個巴赫像是孿生兄弟把關,右邊的一個彷彿被打翻的調色板潑了一身,左邊的一個戴着單眼罩模仿海盜,都穿同樣款色的宮廷長外衣,是一個模式的多種變奏。忽然想起千禧年後,北美洲流行複製的主題,選一種動物做對象,髹上不同色彩,擺放到城市多個角落。記憶中就有牛、熊、海豚⋯⋯恕我直言,拿音樂元老與牲畜相提並論,總覺得褻瀆神明,宣傳部似乎沒有這個顧慮,奇趣就是吸引,古典音樂也不例外。
萬紫千紅
未見到擴音器,巴赫的樂韻卻從天花板漏下來,D大調第五首布蘭登堡協奏曲,起奏的音符像一隊士兵步操過來,倒有點似火車站外與內的步履匆匆。萊比錫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灰色,然而就算評論一本書也不能單靠封面。穿越馬路走過公園,頓時萬紫千紅,萊比錫創辦人繆勒灰濛濛的紀念碑下,花的深紅與蛋黃分外奪目。陋巷裏幼長的鐵枝架起,「三宅一生」,似為露營作好準備,卻是腳踏車的停駐站,到舊市鎮觀光之前,且在這裡休憩一下。兩旁店鋪林立,越南小餐廳過去,是愛爾蘭式酒吧,還有法國的廚具店和德國的雜貨鋪,河水不犯井水。樓房多高四層,一幢二十多層高的樓房平地竄起,想要摩天,路盡頭便開出一個寬闊的廣場,暫時給一個臨時表演台佔據,想是巴赫音樂節的一個項目。路旁的柱頂送來一束青色的石草花。行人路擺滿長方形的泥紅色的石塊,不知道有什麼用途,又有什麼關係?有人坐下來閒話家常,又可以停放更多腳踏車,就當是戶外的家具。探頭進書店,與巴赫的石膏像打個照面,雪白全無色彩,皺著眉似在深思,一首首洗滌性靈的聖樂便這樣想出來,這才是我熟悉的巴赫。路標指向多個旅遊景點,這天我一意朝拜巴赫。心願也不易實現,巴赫的故居已在人間蒸發,眼前這座黃色粉牆﹑棕色窗框的博物館,不過是巴赫在生時對面的鄰居。也好,穿過側廊來到文藝復興風格的入口,仰望托斯卡納柱和門廊,與及用羅利茨斑岩製成的羅馬式拱門,聊勝於無。
音樂遊蹤
巴赫並不是萊比錫唯一的風景,長達五公里的一段音樂遊蹤提醒樂迷放眼世界。走在市面,已經留意到一些不銹鋼的地標,像回力鏢隨意空降地球,彷彿是達文西的密碼,解構之後,都是音樂遊蹤的指引,一時地標就像管風琴的踏瓣,伸腳踩過去,演奏一段萊比錫的輝煌:第一間專業公共圖書館收集巴赫、布拉姆斯和海頓的手稿;樂器博物館藏有最老舊的古鋼琴;孟德爾遜促成德國首間音樂學院;布商格萬豪斯資助公眾組織民間第一個管弦樂團⋯⋯經過戰火蹂躪,很多建築物都被炸毀,鋼琴家克拉拉.舒曼出生的「高挑百合」再不出人頭地,成為音樂史的記憶,重建後的樓房再度空置,那管巧手曾在這裡蜻蜓點水,兩邊的圍板填滿憤慨激昂的塗鴉,一筆一劃都是滄桑。她與羅伯特.舒曼新婚後的愛巢倒還健在,二樓的白色吊燈映照一座大鋼琴,據說舒曼作曲時,最受不了妻子練琴聲的騷擾,一對藝術家結為連理,固然傳為佳話,溫馨之外,依然潛藏着衝突的伏線。舒曼的華采依然不容忽視,是瀕臨瘋癲邊緣的才人,譜寫樂曲之餘,亦為稀有的作曲家會提筆發表音樂理論,總共四卷的《關於音樂及音樂家的論文》,囊括他的藝術觀。
城裡的阿拉伯咖啡樹,是德國最古老的咖啡沙龍,多個世紀以來,詩人、科學家、音樂家雲集,舒曼和「大衛同盟」的成員就經常在這裡研討音樂理論,再把成果交付《新音樂雜誌》登載。消息傳來,「大衛同盟」的成員都是子虛烏有,全是舒曼一人扮演,從不同角度探討同一主題,只為他的天才塗抹上傳奇色彩。在聖尼古拉斯舊校接受教育的理察華格納算不算教而不善?他既創作史詩式歌劇,對愛的迷惘有深切瞭解,對猶太人的種族歧視也排山倒海,教人恩怨難分。在他的慫恿下,孟德爾遜死後的紀念碑,納粹期間就因而摧毀,我們就算沒有給孟德爾遜筆下如仙女般疾走的音符引進仲夏夜的夢境,E小調第六十四首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也溫柔得使人心碎,對華格納又多了一重怨恨,幸虧聖湯瑪斯教堂重修後,建造了一個花瓣般的大門,以孟德爾遜命名,音樂史還算討回一點公道。最出人意表的還是葛里格紀念中心,他遠道從挪威而來,下塌音樂出版商的豪宅奉為貴賓,隔着鐵欄柵,再聽不到他譜撰的皮爾金組曲,他在德國樂迷心中仍然佔一席位,在孟德爾遜紀念館偶爾碰到一場婚禮,鋼琴師演奏的結婚進行曲就是晨歌。
音樂遊蹤的另一個重點是舊市政廳,1723年,巴赫就在這裡的理事會會議廳簽署合約,正式成為聖湯瑪斯教堂的合唱長和音樂總監,趁機說說巴赫與管風琴形而上的默契,管風琴固然留有他演奏的指印,他也擅長驗身,醫治管風琴的傷風咳嗽,加上每星期撰寫新曲面不改容,難怪成為聖湯瑪斯教堂急欲羅致的對象。舊市政廳在1556年落成後,經常樂韻悠揚,喜慶日子,城鎮的吹笛手更樂於獻技。今天我卻無心聽曲,跑到對鄰的舊證券交易所張望。1686年至1687年間,30名商賈根據薩克森自由州建築大師約翰喬治史塔克的藍圖,成立萊比錫第一個商務會議中心,交易所的金色獅頭與配飾,襯托白色粉牆,在陽光下分外璀璨,華爾街式的買賣遇上巴洛克的建築,未必等於俗豔,我就是喜歡那義無反顧的白,急不及待過去一親香澤。屋頂欄杆四角,各有約翰嘉斯柏桑德曼雕刻的石灰岩塑像。朝北的兩個鬼靈精特別惹人注目,拒穿衣服針對市中心,下身用布遮遮掩掩,不知想打什麼歪主意。
美術館本來與音樂無關,卻是音樂遊蹤一個憩腳站,只因為館內藏有麥士克林格爾的貝多芬紀念碑,也就藕斷絲連,克林格爾用了17年的光陰製作紀念碑,是象徵主義的極致,1905年初展時極具爭議性,克林格爾斗膽剝落樂聖的衣衫,坦誠與希臘的神祇看齊,貝多芬駕臨寶座,黃袍只加在下半身,雙腳套着拖鞋,一腳踢向座下的禿鷹,是美與惡的對峙,還是美通過恐怖,試圖與惡和平共存?寶座後有天使臉容頌唱聖歌。這天經過美術館,還有意外收穫,館外恰巧擺放馬庫斯.呂佩爾茨的《貝多芬》,金髮藍臉的貝多芬旁加另一尊人像,卻不是雙頭怪物,呂佩爾茨說要把貝多芬的作曲形象化,人像引頸翹望,似在專心聽演奏,裸肩下欠缺雙手,底下也只有一條腿,呂佩爾茨要暗示,聽音樂主要是腦袋與心靈的活動。
聖湯瑪斯教堂
綠楊移作兩家春,聖湯瑪斯教堂之外,巴赫也曾在附近的聖尼古拉斯教堂擔任合唱長,他的《聖約翰受難曲》和《聖誕清唱劇》更在這教堂初試啼聲。多少年後,聖尼古拉斯教堂要領唱的卻是另一首歌,始自1982年9月,每逢星期一,風雨不改舉行和平禱告,教堂是團體的基地,關注當時社會問題,迅即成為警方和國家安全部的眼中釘,1989年9月4日星期一,約有千人如常參與和平禱告,禮成之後,民權份子在教堂外高舉旗杆,國家安全部要求把旗杆拆除,頓時引起群情洶湧,反覆頌唱「我們會死守在這裡」。音樂遊蹤的告示牌收藏在教堂裡,教徒正在舉行彌撒,我們不想進去騷擾,在外面探頭探腦,無意中與相似的牌匾碰口碰面,細看卻是另一回事。世情就是這樣不可逆料,分散了音樂心,陰差陽錯倒讓我們摸到城市躍動的脈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