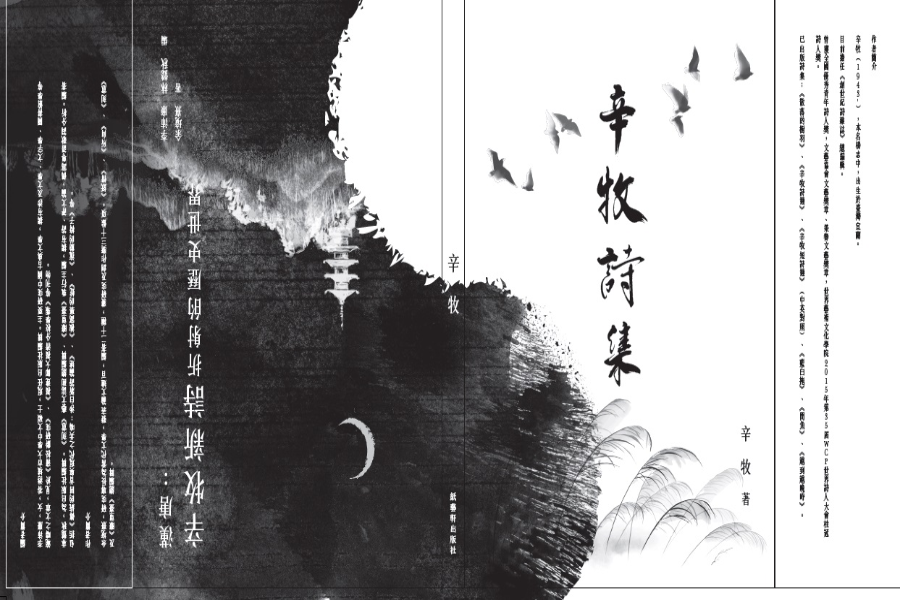路雅最近出版了小說集《流動的椅子》,此書的特色是一書兩冊,如銀幣的正反面。「公面」是小說創作,「字面」是學者余境熹的《順緣掇落花隨圓聽劍聲——路雅小說研析集》。我認為,在無紀律的創作時代,以作品與評論兩隻腳走路是一個很好的方法。猶如我們讀印象派作品,可以有無數的述說,而有水平的畫與文字述說總是互為映照,熠熠生輝的。本書的構想,料也如此。
路雅對小說的實驗具多樣性。當中「故事四:滄浪∙浮生」共由四個極短篇組成:〈遷徙〉〈香格里拉〉〈茶馬古道〉〈寄情〉。學者余境熹說:「平心而論,〈滄浪∙浮生〉並不算容易理解的文本。當中常見路雅刻意為讀者設置的接受障礙。」(頁34)這篇小說無疑是《流動的椅子》裏藝術性最強、技法最奧妙的作品。這個作品,既可以看成是一個整體,也可以獨立為四篇。此外,若不按次序來閱讀,也能發覺當中的意思。這是路雅小說藝術上的一個令人矚目的成就。
第一個是〈遷徙〉1271字。「我」隨家人移民溫哥華,大學遷到匹茲堡。在此認識了年邁的威廉夫婦。而後來,威廉老先生走了,他太太要求我陪同她,一起把他的骨灰撒到校園裏去。第二個是〈茶馬古道〉1204字。齊非隨馬隊經商於茶馬古道上,傍晚歇息在一條村子時,遇上領房的姑娘,酷似他曾經的女人金棠,他拿出當日金棠梳理過秀髮的牛骨梳子,而後來他再走這段茶馬古道時,村子已不見了。第三個是〈香格里拉〉1164字。在香格里拉齊非確實曾經與金棠有過一段情緣,那時齊非是馬幫的一員,他在投宿的悅來飯店遇上金棠。第四個是〈寄情〉1297字。「我」匹茲堡畢業後來了舊金山,並按威廉生前的囑咐,按時寄出那些信。並回想當日與威廉太太安娜對話的內容,知道兩人都曾去過香格里拉。這個小說中的這麼一段,把本來各自獨立的作品勾連起來:
「我在護士訓練學校最後一年的時候,去了香格里拉度假。」安娜一邊把骨灰撒
在園內一邊跌進甜蜜的回憶:「他是基督徒,去那兒作短宣。沒想到我們卻遇上
了。」
從這裏得知,齊非即威廉,金棠即威廉太太安娜。並可以合理的解釋為「前世」的存在。且看下面前世與今生的對照:
|
前世 |
今生 |
|
齊非與金棠 華人 茶馬古道:清光緒年間至民國時期通往昆明西藏瀾滄打洛洵甸等地的茶馬道,是以馬幫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間國際商貿通道。 中國西藏香格里拉 |
(我),威廉與威廉太太安娜 外國人 當代留學之途:香港人崇尚歐美,七十年代以還,常把孩子送往美國等地升學。 美國匹茲堡市 |
路雅這個小說,顛覆了我對小說情節的認知。對小說的審美藝術,一直以來,我重語言而輕情節,認同「現實比小說更荒謬」的看法,我曾寫過一篇叫〈埋怨十二個小說家〉的文章,說:
西洋文評家視小說為虛構的,那只是對情節內容而言,小說所昭示的世相仍是真
實的,甚而較我們生存的世界更為真實……成功的小說家往往能通過虛構把世間
實相浮現出來,優秀的小說家充當了現實的審判官。
四個短篇中,前世的兩個自是虛構,而今生兩個即相對真實。路雅在設定小說場域時,前世選了香格里拉這個具虛構意味的空間,今生的匹茲堡這個鋼鐵之都即是有其現實的投射,這樣的虛實相比,讓小說產生了巨大的張力。也很吻合前生只是虛擬的心理補償,而今生才是缺憾的真實。我們活著,只知道今生的部分,而從不曾知悉所謂的「前世」與「來生」。路雅以其文字,巧布羅網,戳破天機。四篇短小說,相互勾搭,這種既分且合的技法,已然爐火純青。其意旨之高,蘊含之深,推翻了文字的邊界,進入無盡之境。
小說創作並無一成不變的法則。微型小說字數極其局限,一般而言刪枝削葉是金科玉律。在四個連環套中,路雅卻刻意添枝加葉,傳統的作家以為病,然路雅卻用之為技。枝葉的刪或存,可議者不一,然優質的語言是決定存廢的關鍵之一。這是因為美學凌駕所有創作技法。且看以下各篇的述說:
|
遷徙 |
她拿出一把發黃的牛骨小梳,細細地把玩,淡淡的側影,夠不上那梳子讓我吃驚…… |
|
茶馬古道 |
出發前娘給他執拾衣物,每次都是那麼細心,點算着一生一世的關懷,怕撿漏了甚麼。暗暗的油燈照着滿頭霜雪,她晃動的身影貼在震顫的牆上,甚麼都沒說。那張臉無論變得多蒼老,在他眼裏還是澄明如鏡,而她,也該清清楚楚數見他每根髮絲,瞭解他的需要。 |
|
香格里拉 |
離井口不遠處,橫臥着一塊大板石,她來曬書,端正地在上面放上一本又一本。那些不是甚麼珍本,都是近日盛行的詠物、懷人詩詞,美麗而抒情。 |
|
寄情 |
誰去過香格里拉?那裏有我的摯愛真情。夢裏彷彿又見到那藍色的湖,湖水清清, 柳飛依舊。 |
路雅讓小說的意旨隱埋在葳蕤中,這便是學者余境熹所指的「刻意為讀者設置的接受障礙」。這些障礙是藝術抑或敗筆,除了語言外,還得看某些技術性的操作:提供破解障礙的線索,或曰鑰匙。在這篇小說裏,優秀的讀者是可以從小說中找出那把「鑰匙」來:發黃的牛骨小梳。它曾出現在四個小說中。一把小梳,牽引著前世今生的因緣。路雅選「梳」而棄其他,自有寄意。梳子在這裏已然具有象徵的意義,猶如海明威《老人與海》中的大馬林魚,威廉·高汀《蒼蠅王》中的諸多象徵,如島嶼象徵世間的伊甸園等。唐朝白居易便寫過〈花酒〉:「香醅淺酌浮如蟻,雪鬢新梳薄似蟬。為報洛城花酒道,莫辭送老二三年。」雖為古體,其氣韻卻與路雅這篇現代小說相近。梳子帶有對歲月不留人的嘆喟,梳理鬢髮,粘幾根於梳齒間,彷彿讓人看到歲月的流淌。這是梳子的第一層寄意。梳子功用在梳理頭髮,結髮時也得用上。西漢蘇武〈留別妻〉:「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節錄)相贈梳子,常見於熱戀中的男女,託付終生,而最終見證了夫妻間的恩愛。這是梳子的第二層寄意。在小說裏,牛骨小梳的路線與結局如下:
(路線)威廉太太:拿出一把發黃的牛骨小梳,細細地把玩。〈遷徙〉→齊非:
把玩着發黃了的牛骨小梳子。〈茶馬古道〉→金棠:離別時送齊非一把雪白的牛
骨梳子。〈香格里拉〉→威廉先生:把小盒子打開給我看,裏面是一把發黃的牛
骨梳子。〈寄情〉→(結局)我:威廉先生交給我的信亦很快寄完……最後把牛骨
梳子也寄出。〈寄情〉
小說的布局縝密如此。梳子本來只是一件日常器皿,在路雅連番操作後,賦予其極強的藝術意義而成為象徵。小說創作,從來都是對作家的全方位考驗,涵蓋文學與文學之外。平庸者始終在說故事,在榕樹下、在睡榻旁、在爐火側,但優秀者總是回到書齋去,閉門苦思,挑燈伏案,斟酌推敲,浸淫而成。我們不問小說家在說什麼故事,問小說家在思考什麼。法國評論家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 1937-)在〈文學在思考什麼〉一文中說:「正在思考的文學是從寓言(La Fable)的裂縫中發生,它對如何毀滅故事、製造矛盾或是將其化為碎片之類的毫無興趣。它接受了故事本身,並且在它留下的縫隙中安放自身。」(見《文字即垃圾——危機之後的文學》,白輕編,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387。)真是精彩至極。路雅這個作品,在述說一個跨時空的故事時,留下了一個縫隙,即發黃的牛骨梳,讓文本不止於一個故事,而是一種「批判」或「洞見」。
(2023.12.25晚10:30婕樓。)
(附:路雅小說《流動的椅子》及余境熹評論集《順緣掇落花隨圓聽劍聲——路雅小說研析集》,一號兩書。香港紙藝軒出版社。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