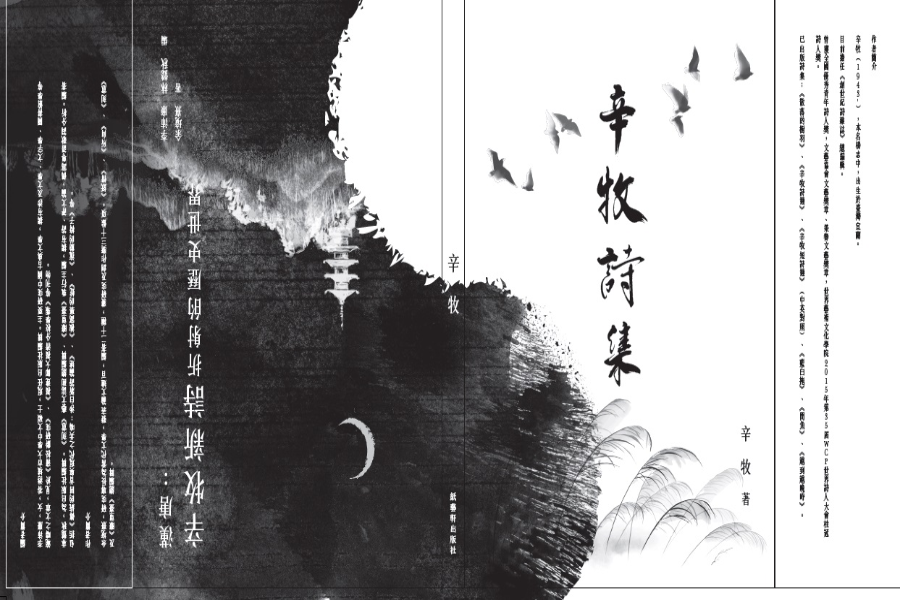在金球獎拿了最佳外語片的《Drive My Car》可謂2021年討論度最高的一套電影,而導演濱口龍介也在繼《偶然與想像》之後,再度極受矚目。濱口龍介一貫地在他的電影裡施展微妙的魔法,而這些魔法也莫名與村上春樹的個人風格十分契合。不過,
要把一則短篇小說改編成三小時的電影,濱口採用了半公路電影的手法,公路電影配合「救贖」的主題,實際已不算新鮮;再者,故事的主要背景是在廣島,也與日本電影在探討傷痛命題時的一般設定吻合。即使這些改編有點意料之內,但濱口最大的武器仍然是他掌握的文本:無論是村上春樹的作品,還是內裡所提到契訶夫的《凡尼亞舅舅》,濱口都巧妙地加以借用,從而發揮了互文性,透過探討文本、戲劇和演戲這三個概念,重新賦予了故事新的意義。
以公路旅程走出傷痛,學習放下最後得到救贖是十分常見的主題,而往往可以真正得到救贖的,不是生者可透徹了解逝者,而是生者可誠實面對自己。誠實面對自己是很多創作者經常討論的議題,而濱口正正選取了以戲劇和演戲的概念去重新切入這個題材,可謂富於巧思。主人公家福在濱口的版本中,既是導演又是演員,而家福那套只讓演員不投放任何感情去讀劇本,直到完全熟練劇本的方法據說也是濱口自己的習慣。從中,我們能一窺濱口對文本的執著。
《凡尼亞舅舅》的原著文本充斥著絕望、消極的人物與封閉的空間,其中所承載的重量正是家福一而再、再而三拒絕再擔演凡尼亞舅舅這一個角色的原因。電影裡出現最多的是家福在車內與亡妻留下來的對台詞錄音帶,而當時的空洞亦更顯《凡尼亞舅舅》原文本所帶出來的感覺。然而,當家福與美沙紀完成了北海道之旅,家福再次回來演出凡尼亞舅舅時,文本有了轉化的意義,而這就歸功於濱口對《凡尼亞舅舅》的設計:相比起傳統的演出,劇中的這套舞台劇邀請了世界各地不同國籍的演員,由他們說著不同的語言,去完成這套超越界線的演出。當中由韓籍啞巴女演員飾演的索尼婭尤其震撼,她與她丈夫在這套戲中恍如天使般的存在,亦同時代表了幸福的定義。當然,
了解劇情便會知道他們曾經歷不幸,但他們的演繹把一切都淨化了,濱口在這裡的選角確可算獨具慧眼。最後啞女演員作為索尼婭向凡尼亞舅舅所說的台詞,便有了轉化的意義,不單將《凡尼亞舅舅》的沉重色彩扭轉,亦回應到《Drive
My Car》 所尋找的救贖:
「我們應當活下去,凡尼亞舅舅。我們應當活過前方無盡的白晝,與漫長的黑夜。無論是此刻,或年老之際,我們應當為他人而無休地工作。我們將以謙卑之姿態迎接我們最後的時刻到來。在超逾我們的墓園之處,我們將坦承我們歷經磨難與淚水。我們的人生是痛苦的。而上帝會憐憫我們。啊。親愛,親愛的舅舅,
我們將活在光明與美好之中。我們將在歡歌笑語中,回首我們在這裡歷經的悲戚。」
這段對白透過手語表現出來,戲院的觀眾都屏著呼吸傾聽,而這段寂靜的吶喊無疑為家福和美沙紀的旅程做了一個最有力量的總結。
濱口的魔幻性仍是我為他著迷之處,而正因為這種特點,也使我認為他最適合改編村上春樹。可是我依然認為北海道那段互訴心聲略為矯情,甚至與整套戲格格不入。有評論指這是濱口的刻意設計,從而去表達對演戲概念的看法,但我就認為這有點「藍色窗簾」了。但無論如何, 以善用文本來說,《Drive My Car》還是把文字的功效發揮到極致,讓講求視覺語言的電影體裁展現出文字的重要性。或許會有人不喜歡,但我仍是十分期待濱口的下一部作品。